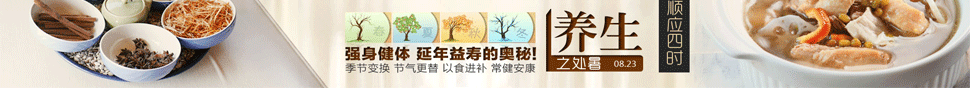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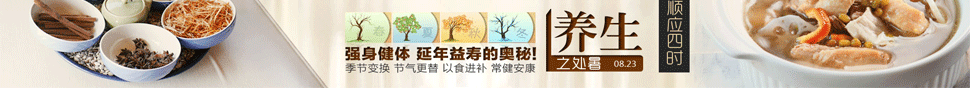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十八岁那年,我远离崇明,去南方上大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这个岛屿一周以上,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远隔离,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来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上海人”这个新的身份是陌生而怪异的,我对这个城市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冷淡、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航运兴衰与认同的转移
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人追溯起来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1],其最初据说来自江南句容县。这些长江口的沙洲默默无闻,按照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原则,长江下游的行政区按长江航道中心线分割,于是崇明在其最初的年里,一直归属江北的扬州路或通州管辖。
这一情况到明初起了变化。年崇明被划归苏州府,年又兼隶太仓州,直至年直属江苏省。这个岛横在长江中央,似乎划给哪边都无不宜,因此在民国年间眼花缭乱地不断变换隶属关系:年曾划归上海特别市,六年后又改划给南通,不出一年再改属松江,年6月解放后再改隶南通。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
行政区划沿革是枯燥的,但这常常反映出主政者对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考虑。像崇明这样隶属关系在四方(南通、苏州、太仓、上海)间不断变换的例子,在中国县级行政沿革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其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碍其对外认同:崇明人自认为“上海人”的已不多,对南通、苏州、太仓的认同感更极浅。这种含混不清的对外身份识别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就文化和地理单元来说,崇明却与江北海门、启东是一整体,彼此更亲切,方言和习俗都基本相同,虽然“他们属于江北”。崇明之所以有不同的命运,与航运有密切的关系。
崇明起初是荒岛,名著于史乘之始,在于元朝时崇明籍海盗朱清率领沙船漕粮航队,开创中国海运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朱清年取海道将南宋库藏图籍运至京师,次年崇明就破格升为州,而在五代、宋时它不过是镇建制,设“天赐盐场”而已。年起,朱清又奉命开海道漕运。不过他没有选择崇明为港口,原因可能有二:1、崇明当时是荒岛,易为咸潮倒灌,产粮有限,选择江南距离产粮地近的港口更有利;2、崇明离海太近,风涛险恶,也无港湾,并非理想港址。——崇明的深水岸线,直到今天也没有发展出一个规模稍大的港口。
元初上海港及青龙港已经淤塞,朱清等人遂选中刘家港,并将此地发展为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市[2]。当时海船路线,是经刘家港后沿内河航道抵达苏州,一时因海运致富者无数,今苏州朱张巷据考即朱清、张瑄之宅址,他们后来又迁居太仓。到郑和下西洋时,刘家港已高度繁荣,但其行政级别却仍然甚低,仅是一卫所(年建太仓卫);于是年割三县地建太仓州,辖崇明县——此时崇明在航运中的地位已下降,年朱元璋以崇明遇潮灾人户减少为由,将其由州降为县。
刘家港自明永乐以后因海禁及倭寇钞掠而日见衰落,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河道泥沙淤积。年后浏河经疏浚一度重现辉煌,但仍未消除淤塞隐患,至年因淤塞太甚,沙船无法停泊,只能移至上海港。不过这个衰落的过程十分缓慢,长达多年。明朝中叶,刘家港有不少崇明商人设立的商号[3],而崇明县城之所以设置于现在这个位置,我以为也与之有极大关联——崇明县城至年后稳定于现址,原因之一显然是此处与刘家港对航几乎成直线,比较便利[4]。
从以上状况分析,当时崇明隶属太仓,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即太仓、崇明以航运而联为一体,其中崇明又出于航海及缉捕海盗的目的而领有长江口各沙洲、岛屿,以便统筹管理。不过随着太仓航运的衰落,这一格局就松动了。尤其自年黄浦江疏浚加阔后,江南的港口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上海。此时崇明的沙船商人仍是主力之一[5],上海的商船会馆,系上海、崇明的沙船商年始建[6],这显示着崇明对外交通的重心已经转移,行政上的变化则略晚15年——年,清政府将苏松太道台衙门由太仓迁移往上海。这一趋势在上海年开埠后更剧烈加速了。其结果是到后来,崇明和太仓之间的轮渡完全断绝,直至年才恢复[7]。对一个岛屿来说,航运的兴衰决定着它对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想象。
上海体验:新想象的形成
上海自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历史,犹如重复了一次太仓在多年前的迅速繁荣景象[8]。自清中叶以来对崇明的引力由此急剧增强,而名义上仍统辖崇明的太仓州至此本身也为上海所吸附。
上海骤然繁荣是基于西方工业基础的,轮船的竞争也使沙船业迅速破产,昔日三大船帮之首的崇明至此一蹶不振,不少人在上海沦落为乞丐[9]。年代,张謇在上海看到黄包车夫,十之八九都是操崇明方言的“通崇海启人”,在那个时代,崇明人到上海多数都已是无产者。至今流传下来的俗话说“到了吴淞,忘了祖宗”、“喝了黄浦水,害了后半世”,这些话中流露着一点辛酸和故作轻松,以及对上海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大城的艰难认同。
由于江海隔阻,崇明人对上海兴起的反应比江南各县要慢一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甲午战争后的两件事:年崇明、吴淞间设置江底电线,始通电报;年沪崇间始辟客轮航线[10]。这对崇明与上海之间的连接所起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更晚一点到年,堡镇地区开始用自动电话。从这一时期开始,崇明的对外交通基本上都转向上海(起初主要是与吴淞,因此吴淞一度占据崇明人对上海想象的中心),而与太仓、南通方向的联系都衰落、甚至切断了。
虽然这些航线有时仍容易阻断[11],时至今日也不免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但重要的是:上海码头至此成为绝大多数崇明人离岛后的第一站,他们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出来,在此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甚少看到当时崇明人对上海体验的感言,不过至少在方言中留下了痕迹。崇明由于孤悬在外,方言比较少受外界影响,逐渐成为吴语方言的一种代表性方言[12],与它历次隶属的南通、苏州、太仓、上海方言均有不同。按照中国方言的一般规律,由于政区内部的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接触,各县方言往往不自觉地向州府治靠拢[13],例如上海方言在元明时推重嘉兴话、清时尚苏州话,现在上海话的地位,是晚清民国后才形成的。
崇明话的孤立状况也是到了与上海密切联系后开始有所转变。崇明话与上海话同属吴语,虽然差别较大(上海人往往听不懂崇明话,但崇明人一般都听得懂上海话,此也可见语言霸权之一斑),有些词汇是共有的,例如“白相”(玩),但上海话中另一些词汇,一般认为是自英语而来,例如“噶三户”(闲谈,gossip)、时髦(smartly)、盎三(差,onsale)、混枪势(chance)、茄门相(没兴趣,German)、红派司(证件,pass)等[14];这些无疑都是在上海形成而后引进到崇明话中来的日常用语。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上海话词汇如“老克拉”(class)、“司的克”(stick)、“白脱”(butter)却不见于崇明话,盖因这些多见于上流社会,引入崇明亦无处可用。
划归上海与知青
年,崇明正式划归上海管辖。不过长江两岸彼此间的陌生感实际上仍未消除。同年,农村人口被禁止移居上海等城市。年我上大学,第一次参加上海同乡会,被问到:“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我答“崇明中学”。对方怔了一下:“崇明中学在哪里?崇明路?”旁边一个大概是虹口区的人笑:“崇明路只有小学。”我有些尴尬,说:“在崇明县啊。”他错愕了一下,继而又低声问旁人:“崇明也属于上海的?”
我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所谓“上海人”一词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并不包括郊县如崇明,一如台湾或科西嘉以“大陆人”概括指本岛以外的本国人。当然这种含义的差别在上海各郊县都多少存在,它们的方言也与上海话有细微差别,只不过在程度上没有那么深,因为崇明在交通和经济上被容纳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上海与崇明的交流自年后的一百多年内,通常都是单向的:大批的崇明人乘船离岛,前往彼岸的大城市,这是崇明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15]。长期以来,上海对崇明的作用,吸纳多于辐射,至今犹然:每年毕业的崇明年轻人,多数前往上海找工作,高中我们班上45人,除了三人回岛,剩下绝大部分在上海。
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对流,则是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上海周围郊县,除了奉贤、南汇有几个农场外,其余2/3的农场都集中于崇明[16]。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农场的运作和在西双版纳、黑龙江等地一样,大多与本地人截然分开,“不与群众争地”,但也因此独立于一隅,生活管理等方面均与周围农村不同(例如农业机械化),仿佛殖民地。
知青对崇明的回忆多数都记得那片土地“荒凉得无法置信”,他们伤感而美好的青春期,那里的辛劳与田园风光,淳朴的老乡,以及多少有点好笑的崇明话(这是上海独脚戏里一个长期的讽刺对象),最后,“青春无悔”。崇明当时是上海的北大荒,简直不像是上海的地方,长江中的长兴、横沙二岛也同样荒凉[17]。至于崇明,直到年代交通仍极不便,年8月,县委书记姚明宝从市农场局到崇明上任,码头上有盛大欢迎仪式,但只见书记在船头挥手,风浪中却怎么也靠不了岸,折腾了三小时无功而返,次日才顺利上岛[18]。
知青下乡,与崇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多,尤其在不靠近农场的乡镇,几乎毫无影响。不过既然来到岛上,难免会有交流,而与崇明人通婚者,即使不多,也有一些案例——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也有接触到过,不过大多数上海人数十年后仍不会说崇明话,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练了两种方言。大部分知青,到年代后都陆续返城。
崇明自划归上海后,四五十年内,基本处于“抛荒”的状态,经济状况已落后于江北诸县,崇明人之愤愤不平,大多由此。不过妨碍崇明对“上海人”这一身份的自觉认同的,主要的仍是历史原因,这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感。有时思及此,不免废然长叹,我也因此理解台湾的“省籍情结”及认同障碍,虽然这并不代表我赞成此种狭隘的地方主义。融合与真正认同感的形成,还是要有待于在交通一体化的基础上文化心理的一体化,有待于新一代更有自信的人群。
-----------------------------------------------------------------------------------------
[1]徐刚《困惑的大芦荡》提到崇明人的祖先是“唐朝武德元年”姚刘两位渔民,故名姚刘沙。文中他还强调“作为崇明岛的农人的儿子,我曾查阅过古本《崇明县志》”。作为崇明籍、又一贯标榜为热爱家乡的作家,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对崇明历史稍有了解者当知:崇明涨露出水面在唐武德年间(非“元年”),但最早记载的上岛居民为年顾、董、施、陆、宋六姓上东、西沙垦殖。至于姚刘沙,则迟至北宋天圣三年(年)才得名,此时离唐初崇明涨现已过去年。
[2]明弘治桑悦《太仓州志》:“宣慰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漕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
[3]道光《刘河镇记略》卷五“盛衰”
[4]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崇明知县张世臣设渡口,一自施翘河至太仓,名长渡;一自南洪至刘家渡,名短渡。各有一船往来。见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
[5]清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嘉庆道光年间沙船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形成“沙船十一邦,均以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年参加漕粮海运的江苏沙船商中,运力超过1万石的24名,其中崇明籍7人,居第一;参陶澍《海运案内急公商埠请加奖励折子》,《陶云汀先生奏疏》卷十五。
[6]辛元欧《上海沙船》第三章“明清沙船业的繁荣及其衰落”
[7]《崇明县志》年版《大事记》:“年1月20日,南门至浏河车客渡航线正式通航,每天一个航次。”
[8]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朱清、张瑄年“浚娄江达海,可通番舶,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咸萃焉。太仓初止数十家,至是称天下第一都会。”这一段景象很类似后来上海开港时。
[9]辛元欧《上海沙船》
[10]《崇明县志》年版交通、邮电两章。按崇明年设无线电局。年9月建淞崇无线电局,我国第一份商用无线电报由此发出。崇籍人从事电信者颇众,崇籍电信专家陶胜百、龚镇六、吴偕骧早就享誉电信界,为崇明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电信人才,各地电话局、电台几乎都有崇籍电信人员供职。抗战前的新疆电台便由崇籍人邹驾白等安装,时有“无崇不成台”之说。
[11]《崇明县志》年版《大事记》记载的上海-崇明航线海难事故有:
年4月5日,行驶于八滧—上海之间的怡生轮,在堡镇东二滧港卸客时倾覆,约20名乘客丧命;
年10月13日,大运号轮装货超载,在堡镇轮埠沉没,死百余人。
年12月8日,崇沪间各商轮因日美发生战事一律停航。
年9月22日夜,由上海驶往堡镇之鸿生轮,在石头沙附近突遭混入船上之武装匪特袭击,军民7人被杀害。
年2月22日,市轮渡7号轮装载稻种靠泊堡镇码头时,因潮涨流急倾没,死8人。
[12]操崇明方言的人口大约在万人左右,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语方言词典系列43本,其中吴语方言8本,崇明话与苏州话、上海话均在其中。
[1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14]薛理勇《上海闲话》
[15]崇明人口年为67.09万,当时包括外沙(今启东);年外沙分立时,崇明本岛人口约40万,启东约32万。到现在,崇明本岛人口64万,仅增长60%,而启东为万,增长%,同期全国人口增长也在%以上。
[16]上海知青下放崇明起始于年,据统计前后有22万人
[17]丁惠增《横沙岛忆旧》:“年10月28日这一天,我乘坐的木头帆船出吴淞口要航行4-5个小时才到横沙岛。当时的码头在新民港,十分简陋。由于近岸水浅、跳板短,我们只得脱下鞋袜、卷起裤管,把行李顶在头上,涉水上岸。”
[18]参张兆田《我的三次“上山下乡”》其中一章“崇明海岛的教师生涯”。文中提到:年崇明条件比他之前插队的西双版纳“不知要好多少倍”,但仍是上海最差的,最突出的是交通不便。他经历过一次,船在江中进退不得,滞留了21个小时!短途客轮不备餐,人人饿晕。此文见《勐龙记忆》,香港文汇出版社5/12版
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句,我的眼睛湿润了,多么相似的经历。我也是19岁离开崇明岛,跨过上海,来到南京上的大学。如今我真的想回崇明岛建一个民宿,加上崇明岛的规划如此符合民宿的定位。花婆婆宣布:海上花岛-上海市崇明岛民宿投资人方案即将发布。敬请期待。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