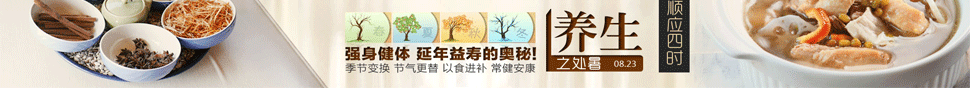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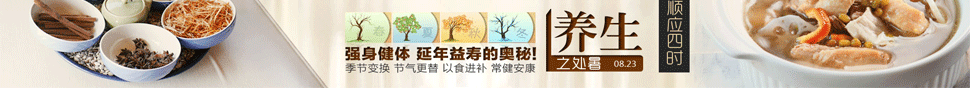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听风楼主
到台北造访梁实秋故居,是我近20年来的一个夙愿。年5月下旬,我与老伴随旅游团飞台湾。6月上旬某日我们在台北,一清早坐地铁赶到台大,在傅斯年墓园默祭后,便寻访到师大路附近的小巷——云和街梁实秋故居。梁实秋故居是一幢日式建筑,四周围着一个庭院,院内一株高大的面包树。大门两旁是约2米出头的大理石立柱,右侧立柱上竖挂着一块金属层贴面的板牌,上书带隶书笔意的“梁实秋先生故居”几个字。
我初闻梁实秋这个名字,是文革前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那时从课本中知道梁先生有一个名号和一顶帽子。梁先生的名号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由鲁迅先生所赐;一顶帽子称“反动文人”,系毛泽东所赠。毛泽东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文字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这顶帽子比他的名号更吓人,但梁实秋的文章似乎从未有人读过。因为这个名号和帽子的缘故,梁实秋在北京、上海、青岛与重庆北碚的故居,也长期无人问津。仅以上海而言,梁先生先后在爱文义路众福里、赫德路安庆坊、爱多亚路弄居住过。但即便当地久居的老上海,有谁知道梁实秋曾在此居住过?文革结束后不久,大陆大批“右派”获摘帽平反,梁先生“反动文人”的帽子始终未摘,“乏走狗”的名号也无人过问。然而进入上世记80年代后,梁先生的散文被大陆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并获广泛好评。人们终于发现一位真实的、作为“五四”以来文章圣手的梁实秋。年11月3日梁先生在台北仙逝,海峡两岸的朋友、学生纷纷作文悼念。至此,“反动文人”的帽子及“乏走狗”的名号,早已不翼而飞。
读梁先生散文最强烈的感受,若用“相见恨晚”四字概括,至少对我而言,毫不夸张。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梁实秋,辛劳笔耕整整一个甲子。除大量散文之外,独力完成莎士比亚全部剧作40册加3卷诗集的翻译,约占38年之久。梁先生的文字隽永、取材自由、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先生下笔无禁区,既写女人善放烟幕的小聪明;写北平小吃如“烤羊肉”、“狮子头”或“拌鸭掌”之类;又写弈棋者从手谈到抱打在墙角,挖取嘴里一“车”的酣战;写沉睡者惊天动地的打鼾声;还写麻将桌上“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谈笑用兵……这一切无不令人哑然失笑。抗战时在重庆北碚,先生的《雅舍小品》风靡山城乃至洛阳纸贵。文如其人,这句话用之于梁先生一点不差。梁先生正是一位宅心宽厚、风趣雅致、学贯中西、又深谙美食的雅士。我读梁先生散文,知道他当年在清华学堂就读时,曾遇到一位国文老师,对他日后文字能力的修练颇有意义。在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一代抗日名将的孙立人,有梁启超之子、后成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
约半个世记后,梁先生定居台北云和街,“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一文即在此问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国文老师的深切眷念。大陆出版梁先生散文集的各种版本,可惜大多未收入这篇上乘之作。文章开头,梁先生给他的国文老师画象:
……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像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型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岂止是漫画,简直是丑化!不过,当你往下再读,却可感受到梁实秋对恩师藏在深处的情感。文章谈这位国文老师的授课情景,早已深深烙在学生永久的记忆中。在讲授课文“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时,“徐老虎”甚至是“眉飞色舞”,完全进入得意忘形的境界。我自己也是多年来教书为业,深知只有极少教师才能随时走入如此忘我的境界。这与那种只知照本宣科的教师相对照,正好形成教师中的两极。“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有一段,谈及这位“徐老虎”在分析课文前的朗读: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象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象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象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
人生得遇这样的良师,大概是前世修来的缘份!当然远不止这些。某次作文课,“徐老虎”在黑板上尚未写好标题,同学中有性急者发问:“这题目怎么写呀?”不料老先生转身冷笑,继而勃然大怒,接着滔滔不绝训斥那同学。大家愕然之间,年少的梁实秋竟按捺不住,挺身分辨几句。这下可惹了祸,老先生将怒火全泼于他头上,在讲台上来回踱着,继而就是开骂。这一席骂,其中警句颇多,令梁实秋终生未忘的一句是:
×××!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
从此,这一警句被同学广泛传诵。只要梁实秋与谁稍有争辨,必有旁观者顺口即祭起这一杀手锏。谁又知,正因这次小小的磨擦,“一眼被看到底”的梁实秋,却成了受益最多的学生。从此后,“徐老虎”批改梁实秋的作文尤其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这位国文老师改作文,“擅长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梁实秋初次经受这大勾大抹,感到挫折,觉得气短心灰。回家仔细揣摩,终于发现文章“虚泡囊肿的地方全被勾抹而去”,留下的竟全是筋骨。“徐老虎”还教了他作文的技巧。譬如文章起笔应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文章写到难分难解处来个譬喻,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即可迎刃而解;文章忌用过多的虚词,该转之处当硬转……
几十年后,文坛早负盛名的梁实秋,对“徐老虎”的怀念依然溢于言表:“如果以后我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文章末尾,梁实秋用淡淡的、略带伤感的笔触,诉出令人感觉绕梁的余音:
我离开先生将近50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的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那年初读这篇“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掩卷之余禁不住感叹良久,甚至有点妒忌梁先生:为什么我偏偏没遇到这样的国文老师?以后再读,想到的是:这样的老师,现今在此岸究竟还有吗?再往后,联想起自己在讲台旁也混了几十年,又深感汗颜。其实真正值得庆幸的是,自己从中年起,总算有机会从容品味梁先生的文字了。
梁实秋故居院内那株高大的面包树,春华秋实、亭亭如盖,茂盛一如当年。树下曾经是梁先生与师大同仁坐而论道、品茶聊天的地方。而今斯人已逝,“此地空余面包树”矣!午餐时间已到,我们另有所约。匆匆告别云和街,脑子里不由得又浮起“徐老虎”可敬可亲的形象:他的“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型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
作者简介
听风楼主,年生。自幼读书,迷迷糊糊,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小学起开始逃学,一路逃到大学。值得自慰的是,文革中从未参与过一次抄家,从未动手打过任何一位“牛鬼蛇神”,从未砸过任何文化遗产,从未多占公家半毛钱好处。逃离大学后,长年教书混饭吃。平生无所事事,至今一技无成。年退休,可算彻底逃离。闲来无事,信笔涂鸦,聊以自娱,消谴余生。expertorscholar原创文章,思想启迪,感谢鼓励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ianbaoshua.com/mbsfb/88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