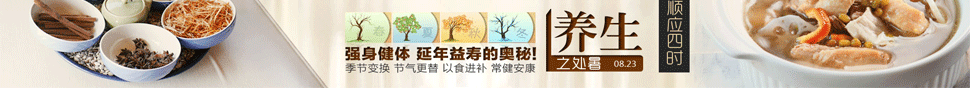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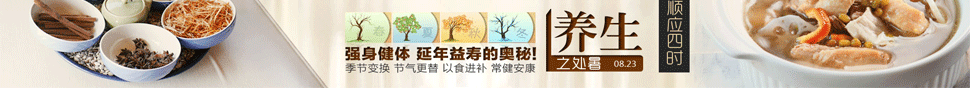
《猴杯》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雨林的故事。作者张贵兴,祖籍广东,生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求学工作于台湾。其中所写的《赛莲之歌》、《群象》、《猴杯》被称为“雨林三部曲”,而《猴杯》被马来西亚和台湾文学界认为是其巅峰之作。
猴杯是一种热带雨林里常见的食肉型植物猪笼草。它的生长需要蛋白质,所以长了个盛满清凉汁液的捕虫瓶。捕虫瓶的香气会吸引大量的昆虫,最后溺毙在汁液里分解成丰富的蛋白质。而丛林里的猴子尤其爱喝里面的汁液,于是别名叫做猴杯。丛林的探险者遇到绝境时也会喝它救急。作者在自序里介绍说世界上有80多种的猪笼草,其中有一半都生长在马来西亚的婆罗洲,有的品种只有婆罗洲独有。大的猪笼草捕虫瓶甚至可以溺毙老鼠和猴子。小说里甚至有当地土著达雅克族将婴孩的尸体放入捕虫瓶汁液里的情景。
猪笼草
作者在自序说,“记忆中的故乡,是一片飞行的,无处着床和不存在的荒原。在绵延粘稠的记忆中,被我写成了不好看的小说,凑成几本卑微的小书。《猴杯》是其中一块飞毯。”
这块飞毯没有带来阿拉丁神灯,没有美丽的公主和华丽的宫殿,也没有想象中浪漫的热带雨林的唯美景致。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毒蝎,遍地的大蜥蜴,盘踞大树大蟒蛇,红毛猩猩,长须猪,无处不在猪笼草,编织着隐秘的罪恶,就像是一部血腥的看不见人性的动植物交织在一起的生长史。
雉是台湾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因为过失被学校开除。他回到马来西亚去看望生孩子的妹妹。却发现妹妹变得陌生而诡异,并且带着不医院逃回了雨林不见踪迹。雉在达雅克族向导巴都的帮助下深入雨林腹地去寻找妹妹。他在代表着土著人村寨的一个又一个的长屋辗转,妹妹没有找回来,却揭开了自己家族和土著人之间延绵了四代的血腥阴暗的恩怨仇杀。
达雅克族人居住的长屋
雉的曾祖父一代是从中国被卖到马来西亚的“猪仔”,他们被转卖到各个矿场、种植园做苦工。曾祖父使用了各种的奸诈卑鄙阴毒的手段,从苦工到承包种植园,拥有自己的种植园,扩大种植园,慢慢积攒了一份家业,也积攒了一份不输当年殖民者的残暴和凶狠,甚至有过而不及。他觉得有了种植园,后代就有了安身立命生根发芽的地方。但世代居住在雨林里的达雅克族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是外族侵扰了自己祖先的山林。他们信手拈来雨林里的百物纹上身体,雕刻在各种的器物上,他们猎取人头挂在门廊上做装饰。而后代胳膊上的猪笼草纹饰成了复仇的象征。于是曾祖父和阿班班,祖父和阿都拉,雉和巴都,你来我往,雨林里的丝绵树、河边的桥身、曾祖父圈养在丝绵树下的野犀牛的皮肤里,嵌满了毒箭、弹头,浮脚楼和长屋遍布弹痕和刀印。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雉想去终止世代的仇恨,但还是倒在了巴都的箭矢下。
纹身和和以犀鸟装饰的大雅克族人
以拉长耳垂为美的达雅克族女人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新奇和复杂,在任何一个有着被殖民和侵略历史,经历了开垦与土著矛盾的土地上都会发生。而《猴杯》奇特之处在于文字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的经历,文字奇诡而狂野,有一种《百年孤独》里的魔幻现实的感觉。但描述的画面和众多的比喻给人心理上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文学体验,这种感觉从头贯穿至尾。有些情节我情愿是作者的夸张和虚构,对于猎杀大象的过程我甚至去百度了一下,没有查到这样虐心的信息,心里稍感安慰。下面仅仅摘录几段对自然景物的描述,以窥探一下这些“黑暗料理”式的文字。
“那晚霞死死地躺在那里,如被蛮荒之狮开膛剖肚的牛羚。”
“云卷如蟹腹,天青如蟹壳。”
“走廊外五点树和炮弹树后的天空像一片烤得焦黑的吐司,抹着草莓酱之类。”
炮弹树
“晴空也很空旷,数朵白云形势混乱,如崩塌的蚁丘;数只闲鹰没什么得失心地划着阴阳交互的太极狩猎图。荒地不见半棵绿色植物,颇似熏烤过的猪皮或鸭皮,漂浮着生蚝似的冷烟,莽丛了无生气像蜕化后的蝉壳或蛇皮。”
“数百块石碑经过火舌梳耙后像一口坏牙暴露野地上,透漏着一种惨笑或喜泣的小丑神情……”
“人胆猪心状石块依旧布满河床上,岸边的根仿佛从死动物身上流出的肠子。”
“原始林,次生林,耕地,废田茅屋,树薯,玉米,香蕉,面包树,木瓜,胡椒,蔗林,野生的,栽种的,两岸风景乱得散瞳。”
“暗夜之猪已经吞尽白日,苍穹极黑而肥,大地多肉,猛禽补钙。”
……
总之,这本书看下来很累,作者自序里说过这是本不好看的小书,原来是真的。当然,不好看不等同于写得不好。
但愿这块飞行的丛林能够落地生根,葳蕤繁茂,被写成好看的小书,哪怕写的不好也是好的,于作者。
水晶菊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mianbaoshua.com/mbsfb/5498.html


